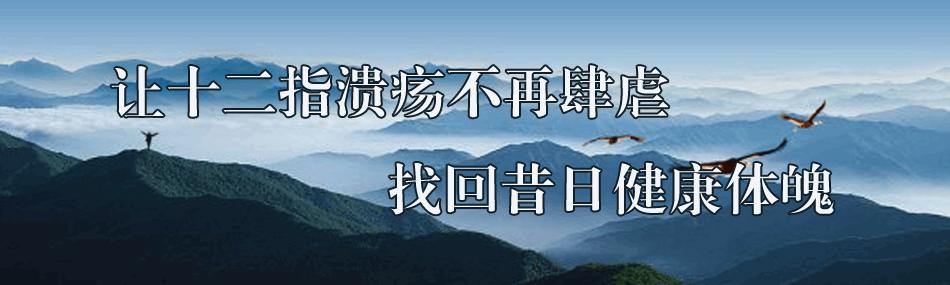红色经典改编想说爱你不容易
“红色经典”改编:想说爱你不容易
近年来,“红色经典”改编热风靡一时。据广电总局统计,从2002年至今,两年间有近40部“红色经典”电视剧列入计划批准立项,共约850集。继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热播并取得好评后,《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刚刚亮相荧屏,《红色娘子军》、《红日》等又已开拍。正在拍摄和行将开拍的“红色经典”,不谋而合地为过去的英雄们加入了当代的许多时尚元素:《林海雪原》将杨子荣变成了一个一身江湖气的伙夫;正在拍摄的《红色娘子军》宣称是一部“青春偶像剧”,等等。这股改编热引发诸多争议,从市井民间到著名作家、剧作家、批评家,纷纭发表看法;广电总局为此连下几道“令牌”,从“认真对待”到“许可证”和“终审”制……为此,本报日前专门召开了一个研讨会,预会的作家、学者和评论家针对“红色经典”改编热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本版摘登专家们的发言精粹与读者分享,以期引发进一步的思考。 参加研讨会专家名单 李钟声(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广东省文艺家批评协会副主席、南方报业团体副总) 陈志红(广东省文艺家批评协会副主席、南方文体中心履行主任) 蒋述卓(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暨南大学副校长) 黄树森(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 金岱(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陈剑晖(华南师范大学出版系主任、教授、《东方文化》副主编) 何继青(广州军区创作室主任、作家) 金敬迈(广州军区作家) 徐南铁(《粤海风》杂志主编) 李凤亮(暨南大学副教授) 钟晓毅(广东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秘书长) 朱燕玲(《花城》杂志室主任) 研讨会背景: 不久前,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发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拉开了“净化荧屏工程”的序幕。4月9日下发的《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红色经典”电视剧要尊重原著精神,不准戏说;遇拿不准的剧目,报总局审查处理。5月25日,又下发了《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了审查管理工作,强调“红色经典”改编剧均需送广电总局终审。凡未经审查的“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一概不得播出。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中国影协、中国视协、中国作协等相继召开评说改编“红色经典”座谈会,预会艺术家、学者、教授给近期的“红色经典”改编热浇了1盆冷水。 座谈会上,专家首先肯定了红色经典的价值和正确的改编原则。文艺评论家李准提出了改编红色经典的基本原则:尊重原著基本的主题、人物关系、故事结构;尊重原著的价值导向;创作改编从现实动身,尊重原著的时代背景。 专家们否定了眼下一些人顶着红色经典的名字,却把自己主观的目的加入其中这类不负的改编。他们认为,现在对红色经典的改编普遍存在着对人性理解的误区。著名导演谢铁骊认为,任意地删改剧情,删添主要人物,创作上“直、露、多、粗”,都不是真正的改编,而是对经典的亵渎。创作首先要依照影视艺术的创作规律,而不应盲目寻求收视率、票房,疏忽了影视艺术引导、启发、提高观众欣赏能力的作用。评判艺术作品的审美标准由利润标准取代,这类做法的危险性可能一时不明显,但是久而久之,其危害是我们几代人也还不清的。 陈志红(主持人): “红色经典”改编热引发的思考 所谓“红色经典”是一个新生成的概念,指的主要是创作于解放后、改革开放前的一些在读者和观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以反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为主题的文艺作品。近年来,在文艺创作领域,一些“红色经典”作品被重新改编或改写,比较引人注目的有《沙家浜》、《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等,这些改编或改写,或在原来的故事情节上增加了新的情节,或对原来的人物关系进行重新设计,这些改动,在价值取向、审美情趣上很大程度地改变了原作品在读者和观众心目中的固有形象,因此也在读者和观众中产生了很多疑问和争议。这些疑问和争议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如何历史地看待这些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艺作品?2、改编这些已成为固定的历史文本的作品意义何在?3、这类改编热是历史与文化的自觉选择还是市场操作的结果?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上述的每个问题都是一个大命题,它与一些基本的文艺理论问题也是息息相关的。如文艺创作中的历史与现实关系、艺术的真实性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方召开这个研讨会,请各位专家学者就这些文化热门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通过这类探讨,一方面能够在批评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也希望将讨论进一步展开和深入。 李钟声: 应提升文学批评的影响力 近来,“红色经典”改编热在社会上引发很多争议。这是新的社会形态下的必定现象。现在是多元化的时期,文学流变很快,这些现象和有关问题的出现都不足为怪。作为媒体,本报一直对这个问题予以十分的关注。上周,我们的已就长篇小说和电视连续剧《红色娘子军》的出版和热拍,采访了金敬迈、郭小东和赵江等作家,让他们谈了各自的看法,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谈深谈透。今天我们约请大家来,继续就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希望大家在各抒己见的同时,也为我们做做顾问,出出点子,共同为活跃广东文坛、进一步提升文学批评本身的影响力而出力。 “红色经典”是意识形态的符号,一旦解构,就意味着对历史的颠覆 蒋述卓:对“红色经典”的改编应当慎重。我认为,“红色经典”大多反应了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一段历史,是一种历史的沉淀,是意识形态的某种符号,一旦解构,就意味着对历史的颠覆。不是不可以改编,但应遵守一定的艺术规律。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红色娘子军》,在原电影的基础上,丰富人物的身世和情感的描述,这是可以的。但发表在《江南》杂志的《沙家浜》,写阿庆嫂与胡传魁是情人关系,则完全是对历史的颠覆了。 何继青:对产生于上世纪5六十年代、曾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作品进行改编完全是可以的。包括古典名著、外国经典名著的改编,国内外都有很多成功的范例。这也是满足广大文化消费者日趋增长的需要。但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合适改编。像《红色娘子军》,从90分钟的电影改编成20集的电视连续剧,我觉得十分困难。就像一杯美酒加了其它东西,这杯酒还能有原来的味道吗? 从技术层面上讲,我认为对“红色经典”的改编应遵守“三变三不变”的原则: 1是作品原作中的道德观、价值观和理想信念不能变;2是人物的基本形象不能变,观众认定的就是原有的人物形象。如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中杨子荣,给战友下巴豆、使绊子,连人物的品格都有所改变了,观众就难以接受;3是人物关系不能变。三变是:改编者的认识观要变。如果作者的思想深度和认识高度还停留在当年原著的水平,观众也不买账;改编者在叙述方式上要变。如果还是老一套的手法,也吸引不了观众;在人物的精神情感的描述方面要变。过去的作品由于各种缘由,在这方面大多是疏忽的。 徐南铁:现在对过去作品的改编,可以说,是现今某种社会现实的反应,或将某种社会心理投射到过去作品的人物身上。我觉得没有必要拿文学的高度来要求所有的作品。如《江南》杂志发表的《沙家浜》,有人说写出了阿庆嫂人性的丰富和复杂性。写人物的中间状态,在文学创作上这个禁区不是早就突破了么? 黄树森:从文学史来讲,历史改编太多了。1961年,光是写《卧薪尝胆》的剧本就有100多个,其中包括有9种开头,3种结局。将历史故事和长篇小说改编成电视剧,这在文学创作中有补充的功能。目前,牵涉重大历史问题的改编不多,意识形态上还是应当有这个宽限度。至于在人物关系、情节上的移动,改编是很难避免的。由于改编本身是应当有创造性的,但也不能天马行空,太随便了。如果每次改编都能引发争鸣,这对艺术的发展也是一种推动。 对“红色经典”的改编有没有价值和意义? 金敬迈:产生于上世纪5六十年代的许多作品,无不打上当时那个时期的烙印。《红色娘子军》最初的版本里有一段女兵们手捧《为人民服务》的小册子舞蹈的片断就是由于政治的需要硬加上去的。1930年哪有《为人民服务》?用与时俱进的观点来看,那个时期的作品人物僵化,艺术表现手法陈腐,毛病不知有多少,根本不值得改编。我反对一切改编。有出息的作家不需要改编他人的东西,何必拾人牙慧、踩着他人的肩膀博出名呢?改编热纯洁是一伙想出名、想赚钱的人营建起来的。 陈剑晖:那些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品,称“红色”是可以的,但不一定是“经典”。那些作品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含有较强的政治干预的目的,是意识形态合谋的结果。从文学性来看,它们其实不具有“经典”的资历,改编是没有太大的价值和太大的意义的。 金岱:我认为,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应搞清楚“改编”这个词的涵义,现在有些这方面的作品不一定是改编,而是“借题”,那些戏说,仿作之类都是“借题”,而不是改编,例如《沙家浜》的小说“改编”,我看更多是“借题”,有些过去的电影要改编成长篇小说,“借题”的成分应当也是会比较大些。“借题”作为一种策略,是想要消解点甚么,乃至颠覆点甚么,都可能,这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不好一概而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借题”要非常奇妙,非常有意思,非常成功,绝非一件易事,“借题”成为一种热是不太可能的。 从本来意义上的改编来讲,则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1是完全的市场需要,改编者看准了市场,只要符合有关版权的法律,不违背有关政策,尽可以听其自便。但我不相信今天市场真会出现一个“红色经典”改编热的需要。2是意识形态的需要,意识形态今天会需要通过重塑那些革命“经典”,来加强主旋律,强化向心力吗?我想不会有这样的需要。如果真这么去做,也不是上策。3是从纯洁艺术的角度看,有艺术家认为5六十年代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作品中的确有艺术上品,值得来重新打磨,或值得通过转换艺术情势来加以探索或传播,则无疑是应当去进行的,而这就必须要有精心地选择,不会所有过去热过了的作品今天都重新热一遍。 所以,我不认为,“红色经典改编热”,会真的热起来。 李凤亮:对“红色经典”的改编是非常有价值的。我认为,有关“红色经典”改编的争辩,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价值转型期不同话语立场、文化气力、利益观念相冲突的表现,是大众文化条件下艺术创作政治性、艺术性及商业性在撞击中谋求调和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讲,探讨改编的艺术性固然重要,但更有分析价值的是改编背后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察“红色经典”改编的意义。其一,是在艺术创作层面,“红色经典”改编提示我们重新思考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艺术真实性、纪实作品的公道虚构、艺术情势间的互动(如电影、小说、戏剧等的相互改编)、创作主体的著作权等一系列问题,固然还包括如何对待既定文本、处理其精神价值等问题。其二,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红色经典”改编引发出意识形态怎样对待艺术自由、艺术创作如何建构意识形态的问题。从现有改编作品看,对待原作所反应的主流意识形态有三种态度:1是建构性的,通过形式上的创造来巩固、加强原作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等。二是重构性的,在内容上丰富原作,为传统的阶级叙事添加更多的人性叙事或文化叙事,通过叙事角度的改变,使原作的意义得到转移和深化,如《林海雪原》、《一个和八个》、《红色娘子军》等,这两方面的改编占据了主流。3是解构性的,即通过后现代的“戏拟”、“拼贴”,淡化乃至消解原作的精神立场,这类解构性改编引发的争议最大,如小说《沙家浜》对原作的改编。 “红色经典”改编热是某种社会心理的投射 蒋述卓:目前为何会构成“红色经典”改编热?我觉得是为了逢迎社会上很多人的“怀旧”的心理需要,以提高收视率为目的而掀起的一阵风潮。听说《红岩》、《青春之歌》也在改编进程中。我坚持改编应遵守一定的规则去做,改得好,对过去的那段历史也是一种普及,能给后人留下更多的思索。 徐南铁:目前有的作品的改编,将原有的价值观念完全颠倒过来,不由让人心生疑虑:它到底是把历史事件还原了,还是更加曲解了?这些改编者更多地是为了抢夺眼球,出于对利润的追逐而这样做。但同时,这也是对目前多元化的大众文化消费的一种满足。 钟晓毅:“红色经典”改编热是两种因素协力推动的结果。一是上世纪8九十年代,“戏仿”(戏说、模仿)的风潮从影视界吹到文学界,如《我的帝王生涯》,就是对文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颠覆之作;《沙家浜》是“戏说”,或说是“重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编。2是由于文化消费市场的需要。我们正处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人们的消费需求也是多元的。目前,改编热是世界上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并且将会愈来愈热。 朱燕玲:改编这类事,应当说是一种普遍现象。前些年很热的有《大话西游》,现在有《水煮三国》,为何就恰恰将“红色经典”的改编拿出来讨论呢?这与“红色经典”作品中凝聚了数代人曾有过的生活记忆有关。改编热的兴起,说明了当下的作品不足以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文化经营者们就把过去的东西拿来重新包装推出市场。本社这次推出郭小东的长篇小说《红色娘子军》,就考虑到它是本土的东西(原作者梁信是广州军区的作家),既配合同名电视连续剧的播出,又逢迎了人们“怀旧”的心理需要。 “红色经典”改编热的产生,是否是有市场这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 黄树森:在如今的市场经济时代,传媒需要市场,作为文化产业的影白癜风原因视业更需要市场。改编热的兴起正是顺应了市场的需求。现在连好莱坞也掀起了改编的热潮。这类热潮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影视业既然要走文化产业之路,不但“红色经典”的改编成为热潮,任何东西都会被挖出来改编。刚开始可能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经过市场的大浪淘沙,经过时间的检验,留下的都是有水平、能被观众认可和接受的东西。 陈志红:可以说,现在是建国以来文艺创作氛围最为宽松的时期。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全部社会处于转型期、文化领域也不断产业化,被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操纵的情况下,文艺创作也出现了很多使人耽忧的现象,一些作品在价值观上游移不定,对崇高精神的消解,对传统美德的抛弃,在张扬人性的名目下日趋露骨的性描述,对历史的充满虚无主义的“戏说”等等,占据了人们文化生活的相当部份的空间,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构成,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在文艺创作上既多元又复杂的时期,需要文艺批评家、理论家们十分当心、细致的分析和梳理。 陈剑晖:“红色经典”改编热是出版商和影视制作人捉住社会上“怀旧”思潮的契机,逢迎某种政治需要加上经济效益的寻求,对“红色经典”加以包装的结果。 何继青:“红色经典”改编热,是市场现象,不是谁造成的,而是市场自然构成的。前两年也拍了《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但没有热起来。这两年各地都提出要建文化大省、建文化强省,这是好事情。要发展文化事业,不发展文化产业不行。电视剧作为面向市场的大的文化产业,一定要受市场所安排,不应只为文化生产的指挥者和领导者生产产品,而应为广大文化消费者来生产。所以改编甚么、怎样改,都应当斟酌市场的需要。 李凤亮:就名称而言,“红色经典”改编的意识形态指向是相当明显的,但其市场性特点却更加本质。它逢迎和满足的,是人们“怀旧性”的文化消费。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话题,从好莱坞电影的英雄叙事、道德叙事,到当代中国的“红色经典”改编,我们可以触摸到全球性的大众文化消费潮流。经典改编满足了人们的“文化怀旧”愿望,它实际上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老歌热”、“老照片热”、历史文化热的一个延续,《豪情燃烧的岁月》的热播、学术界有关“上海文化”的热读,也都是在这1潮流下构成的文化现象。 梁信:如果“红色经典”变了色彩,那就可悲了 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原著作者梁信、电视剧本改编者之一及同名长篇小说作者郭小东因故未能到座谈会现场,通过分别采访了他们。 :您作为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原著作者,对“红色经典”改编热是怎样看的? 梁信:对“红色经典”剧的改编、重拍,以适应今天的观众和世界的观众,我是赞同的。但是,如果把“红色经典”改成了桃色经典或黄色经典,把影响了几代人的英雄人物改得不伦不类,那就可悲了。 几年前曾有人让我将电影剧本改编扩充为20集电视连续剧本,我断续完成了,然后就被买断了电视剧本改编权。现在拍的是用了谁的本子,我不知道,也没看过。投资方和主创人员我也一概不知。所以我对改编后的剧没法评价。 播出的剧我只看过《林海雪原》,而且也只断续看了几集,感觉线索较乱,也不敢妄加评论……这些固然都不是主要的,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剧的放映引发杨子荣家乡人的强烈反感,引出了国家广电局的“红色经典”剧改编许可证制度――今后这类剧开拍要有许可,拍完要经终审。 :那末您改编的20集剧本是如何在原著基础上扩充、丰富的? 梁信:主要是增加一些人物的生活经历,各种人物再造,同时也增加了4、5个配角……20集的剧一两句话说不清,但我的原则是不要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这代人的笔下固然是不会脱离那个时期的。这个剧本将来或许会出版,要根据我的健康情况来看,我也在断续整理自己几千万字的手稿和发表过的作品,可能会出一个作品选集。 :您对郭小东和晓剑著的同名长篇小说如何评价呢?我看到书里附了一封您的授权信。 梁信:我同意他改编。《红色娘子军》这个题材有人要去写它、丰富它,我觉得是好事,至于写的怎样、改成什么样,我没有精力去看,郭小东写完初稿寄给我看过,我也没看。我同意他改,不收版权费、不署名,也不拿稿费。这些年来,《红色娘子军》的改编有很多,光是京剧就有两个版本,还有昆剧等等,我从没追究过版权的问题。 郭小东: 时期不同了,老戏新编固然应当有所不同 :您作为《红色娘子军》长篇小说作者和电视剧本改编者之一,对小说和剧本哪一个更满意? 郭小东:我对小说比较满意,剧本是一个集体创造的产物,不能够更多反应个人的意图。比如在电视剧《红色娘子军》策划书中,我曾意欲将之改编为一部中国版的《这里的拂晓静悄悄》,加进一个崭新的现代视角,从现代人的角度去审视原来的故事。但这个初衷没有被制作方认可,但在我的小说中实现了,小说除丰富了原有人物和情节,还加了一个新的视点,虚拟的吴琼花的孙女、南霸天的孙子,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的视点,一虚一实、1主一次两条线,历史和现实的交织,更有利于故事展开,更有利于变换视角、评价历史。 :那末在您的心目中理专业治疗白癜风的医院想的改编应当是什么? 郭小东:梁信的电影剧本包括着人本的因素,但这些因素由于时期的原因被封闭起来了。40年过去了,我想应当释放它们。“红色经典”的文学局限是不言而喻的,原来的浏览记忆也是有缺点的,以现代人的审视再度创作,重新确立一个视点,还是原来的故事、人物,但已是人本的、真实的故事,是被释放的充满人间精气的人物。所以我们的任务是买通被梗塞的地方。固然,不能离原来的故事太远。你只能在原来的故事里寻觅被封闭阻塞没有释放却一定可以、也应当买通的东西。而且“红色经典”在这些方面常常都规定得比较完善,明确,纯洁。正由于原来的这类定位,也就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打开的可能性。
转载注明: http://www.jwoas.com/jbzz/1009.html
- 上一篇文章: 第六届中国深圳文博会湛江市取得优秀组织奖
- 下一篇文章: 聂远难道就是新唐僧图